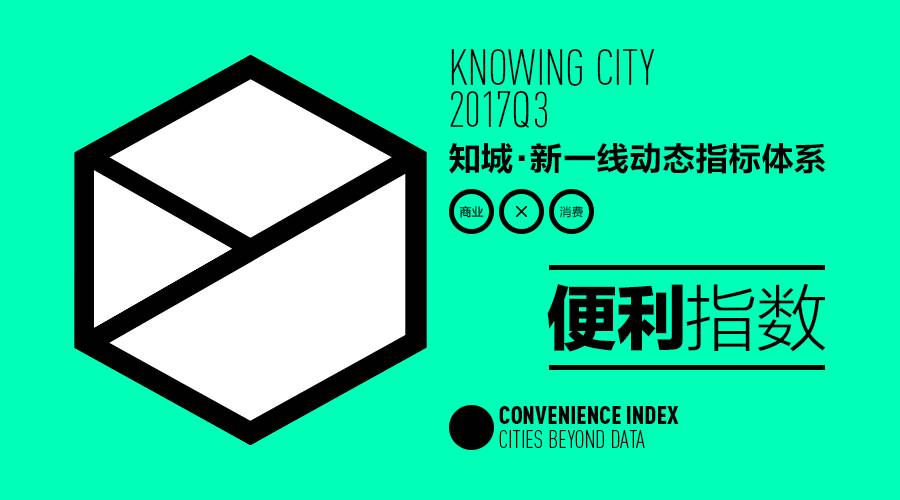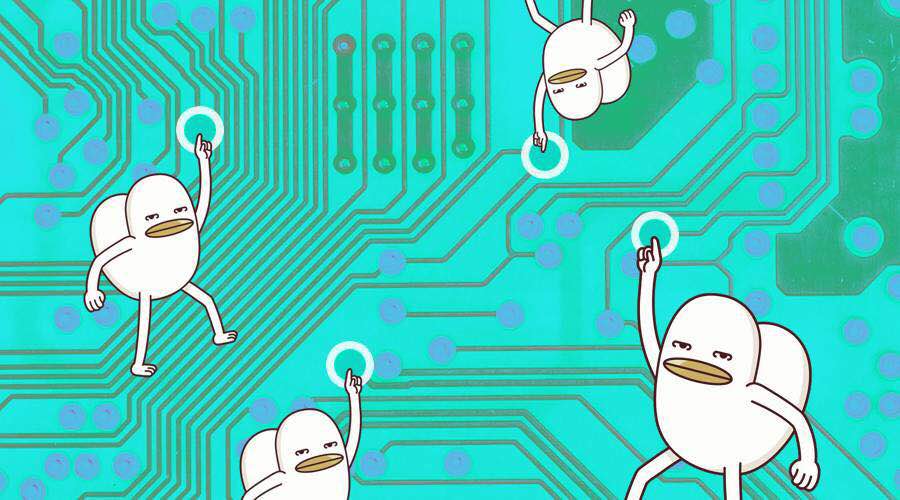机场商业可以算作城市里的一个重要商圈吗?每次做城市商圈分析的时候新一酱都要犹豫一下。
毕竟当机场商业做到了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水平,其商业氛围和体验度甚至可以超过一般城市商业体的能量——樟宜机场最新对外开放的航站楼前综合体“星耀樟宜”将280家店铺、游乐体验设施和热带雨林一起装进了一个13.7万平方米的玻璃建筑里。
但在更多的中国城市,机场商业还处于发育阶段。在坐飞机出行更为日常的城市里,机场商业自然会随着客流和需求的增长不断升级,而在客流量较低的低线城市机场,80块钱一碗面的刚需型“商业设施”依然是主导。
想要理解机场商业的发展,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当前国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排名。
按照一般的城市商业体日均5万人次的客流计算,它们的年客流量也只能是几个头部机场的零头。对于拥有天然的大客流优势的机场来说,服务好这些每年仍在持续增长的客流的基本出行需求之外,进一步抓住他们停留在航站楼内的时间,则能带来不小的“非航收入(即非航行性收入)”。
根据戴德梁行在《大航空新机遇报告》中提到的数据,东京机场、香港机场和悉尼机场的非航收入占比分别达到了74%、66%和57%。非航收入中除去广告业务,最有发展价值的就是机场商业。
新一酱花了一点时间从高德地图获取了85座国内机场的商业门店POI。从总量上看,北京首都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的商户数量都超过了400家。
进一步考虑每座机场的客流状况,可以看到机场商业资源对客流的服务情况。
北京首都机场由于旅客量早已超过设计的8300万人次,达到亿人次级别,它当前的旅客与商业资源配比明显低于商户总量相当的广州白云机场。上海浦东拥有仅次于北京首都的第二大客流,但其商业能力也低于广州白云和昆明长水,每百万人次客流拥有的商业资源不足4家。
随着中国城市中一批头部机场遇到客流瓶颈,能够在机场商业上提供更好服务的通常都是建设时间更近的机场。昆明长水、广州白云和深圳宝安是三座当前单位客流商业资源配置最好的机场,它们都是2012以后进行扩建和重新招商的。
相比于城市里的商业体,机场商业有自己的特殊性。除了安全方面的要求,机场内的消费场景与城市商业不同是很重要的因素,这直接影响着机场商业的业态布局。
新一酱在85座机场的3913家店铺中找到了260家特产店,这个数字占到了所有购物型业态的10.27%。特产店数量最多的机场是昆明长水,一共有33家。
在最早期的机场商业经营理念中,特产、手信等都是典型的出行消费场景——到一座陌生的城市出差、旅游总要带一些和当地相关的东西回去。但随着航空出行的日常化,我们需要在机场完成这样的消费场景的比例变低了,更重要的需求变成了与城市商业类似的“消磨时光”。
餐饮业态在新一酱统计的机场中整体占比达到了30%,这与一般的购物中心类似。不过其中咖啡厅和快餐厅的比重加起来接近一半,制作相对繁琐,又有一定保温要求的中餐厅比例还是明显低于大多数城市购物中心。
要在机场开一家店,租金并不便宜。“几乎所有机场的商铺租金都可以和它所在城市核心商圈的最高租金持平。”戴德梁行中国区商业地产部董事总经理甄仕奇说。
上图中“品牌专卖店”的分类中有很多中高端品牌,你可能也经常会在各地机场人流量最大的位置看到它们。虽然通常这些门店在机场的生意并不好做,“但在机场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品牌露出的广告价值可能更高,品牌方也就愿意为了门店附加的广告价值支付超出它们实际承租能力的租金。”甄仕奇说。
新一酱在机场品牌的偏好榜上也发现了一些平时见不到的品牌,比如蔚蓝书店、经纬书店,还有机场里占有率第二的便利店品牌航诚和零售购物品牌首信。这些频繁出现在机场的品牌大多也都只存在于机场。
它们之中有不少其实是机场集团的自营品牌,也有一些是针对机场的招商方式专门运营的品牌。就甄仕奇的经验来看,这背后的原因与国内大多数机场一直采取招标制而非市场化招商的方式来安排商铺租户有很大的关系,“机场商铺招标制度的原则就是价高即得,而且有一套庞杂的流程,对习惯了商业谈判的品牌来说过于复杂。这使得以前很多机场品牌都由机场自营,或者由专门的代理商运营。”
机场商铺招标制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变,这从机场内包含的连锁品牌数量就可以看到。如果将上海市范围内拥有三家以上门店的品牌定义为连锁品牌,连锁品牌的确不是机场商业的主流,浦东机场的连锁品牌仅占所品牌数量的一半不到。
这些出现在机场里的连锁品牌,构成了机场商业和城市购物中心之间的差异。
我们进一步计算了上海浦东机场内的商户与几个上海购物中心的连锁品牌重复度。其中重复度最高的iapm和正大广场也只有7%——如果看绝对数量的话,新世界百货和龙之梦购物中心有超过30个品牌同时出现在浦东机场里。
相对缺乏市场化、连锁型品牌的进驻,也是国内大部分机场内价格水平偏高、服务意识较低的原因。
新一酱从机场里的连锁品牌和机场自有品牌中分别选了星巴克、肯德基和星阳舫、紫悦这4个门店数量最多的餐饮品牌统计它们的人均价格。很明显的,两个机场品牌的价格明显更高。
我们也同步计算了机场里关键词为“牛肉面“和“咖啡馆”这两个餐饮类别的整体价格,它们的平均价格分别为48元和62元。与城市内同类商铺比较,机场内餐饮的价格依然偏高,而从评论的词频数据看,机场餐厅的味道、服务、环境以及便利度等依然是大家最希望得到满足的关键词。
一个好消息是,人们对于机场商业的价格和服务质量的困扰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甄仕奇和他的团队以第三方招商代理服务的身份参与了深圳宝安机场T3航站楼的招商,作为熟悉城市商业地产运营方式的招商团队,他们的介入也让机场的商铺运营融入了更多市场化的思维。
“我们在深圳宝安机场的招商中引入了洽谈制,这让很多过去认为机场招标流程复杂而不愿意尝试的品牌有了参与的积极性。机场运营方也不再局限在过去’三个盖子盖四个锅’的固定商户资源池里了。”甄仕奇说,深圳宝安机场也是境内首个采取这种方式招商的机场。此外,他们也根据人流到达与出发的不同属性,制定了更合理的业态配比,并重新划分机场商铺,增加了更多面积较小的商铺。
喜茶是宝安机场新引入的一个典型市场化租户,它就在旅客安检后必经的主通道上。按照机场过去商户招标“价高者得”的逻辑,这个位置原本很可能属于奢侈品品牌。“机场商业现在开始更多关注旅客的需求了。”甄仕奇告诉新一酱,深圳宝安机场也对连锁品牌提出了“同城同价”的价格要求。
更合理的商户布局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变化。新一酱整理了上海浦东机场和深圳宝安机场的业态结构。
简单的数量对比就能看到,2013年正式启用的深圳宝安机场T3航站楼(相比浦东单个航站楼)拥有更多的餐厅,并且在安检前配置了更多的商铺——最新开业的超级物种也被安排在这一区域。
对国内机场的商业发展来说,一个新的机会正在出现。目前国内在建的大型机场基本都将旅客的出发和到达安排在了同一层,在甄仕奇看来,这种混流机场的设计对机场商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利好,“尤其是对于候机区的商户来说,经过的客流直接翻了一倍,商业氛围和旅客的乘机体验都会有很大的提升。”